-
查看详情
散文:《蒜田里的银铃铛》
更新时间:2025-07-03
晨雾还裹着蒜叶的露水时,母亲已经蹲在蒜地垄头了。她的袖口挽到肘部,衣服沾着泥渍,手指像两根灵活的小耙子,顺着蒜叶根往土里一探,再轻轻一掰——白生生的蒜头就带着湿土滚出来,裹着碎草叶,像刚从澡盆里捞起的胖娃娃。
我站在地头的杨树下,看父亲拿着铁铲子从家里过来。他的布鞋踩过田埂,泥点子溅到裤管上,叠成深一块浅一块的地图。“丫,把水壶递过来!”母亲抬头喊我,额前的碎发沾着汗珠,泛着细亮的光。她身后已经垒成长龙,里面码着刚拔的蒜,叶尖上的露水顺着往下淌,地上印出一道深色的线。
日头爬到头顶时,蒜地蒸腾起湿热的土蒜味。父亲的铁铲子划开板结的土块,“咔嗒”一声碰到蒜根,他就弯腰用手拔。他把铲松的蒜一棵棵拔起,抖落泥土,再将蒜叶在手里绕个圈,编成小辫挂在田垄边的铁丝上。风掠过蒜叶,成串的蒜头晃啊晃,像挂了满树的银铃铛。
“歇会儿吧。”母亲从袋子里掏出几张煎饼,抹上酱,又加了点小菜。父亲坐在田埂上,啃着饼,突然笑:“你瞅这蒜头,比去年大一圈!”他掰下一个,用拇指蹭掉表皮的泥,露出瓷白的蒜瓣,“听说今年蒜收购价能到四五块,七亩地怎么也能收一万八千来斤,算下来......”他掏出手机计算器,用沾着泥的手指划拉,“一万八乘四块五,八万一!够给儿子的新房子装修了,呵呵。”
母亲的手顿了顿。她的指甲缝里全是泥,指节因为常年弯曲使劲有些变形,可此刻却抿着嘴笑:“这次买四开门的冰箱,能多装点东西。”风掀起她的防晒衣角,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短袖——那是我刚参加工作买给她的,她说“软和,干活得劲”。
傍晚收工,院子里堆着小山似的蒜辫。母亲烧了热水,父亲蹲在台阶上歇脚。母亲擦着汗往锅里下饺子:“等卖了钱,先给你自己买双新运动鞋,这双底都要开胶了。”父亲梗着脖子笑:“买啥新的?补补还能穿!”
月光爬上院角的石榴树时,我躺在堂屋的床上,听父母在院子里对话,母亲:“可看着这堆蒜,咋就不觉得累呢?“父亲:“咱农民,不就图个收字?春种一粒子,秋收万担粮,这蒜啊,就是咱的盼头。”
收蒜季的故事,从来不是汗水的独白。它是父母弯成弓的脊背,是蒜辫碰撞的脆响,是算盘珠子拨出的希望,是所有辛苦都有回响的笃定。又是一年收蒜时,七亩地里的每一颗蒜头,都藏着一个关于丰收、关于爱、关于美好生活的约定——它们在泥土里扎根,在阳光下生长,最后,变成父母眼角的笑纹,变成面对生活变数的底气,变成我们家越来越亮堂的路。(邳州农商银行 宋春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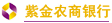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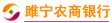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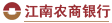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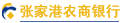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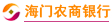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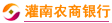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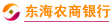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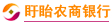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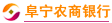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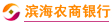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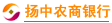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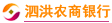












 2025年07月03日
2025年07月0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