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看详情
随笔:《樟木箱与零钱罐》
更新时间:2020-04-16
南门街未拆迁时,曾居住过的四开间平房西屋内,有个外婆的宝贝樟木箱,母亲告诉我那是外婆当年的嫁妆。箱子呈长方形,表面暗红,正前方有个铜质锁孔,透过锁孔朝里瞄,漆黑黑的。只有当外婆用那把沉甸甸的黄铜钥匙插入锁孔一卡一拉再向下一按时,那里面的名堂才被我看得分明。
这钥匙藏的地方,外婆只告诉了我。樟木箱子里除了我小时候的小金木鱼儿和外婆说要传给我的小金首饰外,还有只泛黑的铁皮翻盖盒子,里面的东西是我出生前的老物件,我便总捣腾出来玩。不同的毛主席头像纪念徽章上有各种图案,外婆会一个个讲上面来历,印象比较深的是其中一只带芒果的徽章,外婆说那是当年有人献给毛主席的,那个年代的人们常把认为宝贵的东西赠送给敬仰的人。盒子里还有一些破旧铜板,有的已看不清图案,便总被我挑来让母亲插上鸡毛做毽子踢。小时候物资匮乏,但心灵手巧的家人,总会变着花样让我快乐。外公说,那些铜板看似已经无用,可是在解放前却是生计,要是有人有个圆大头可就了不得了。母亲还曾说过,外婆原有一只珍爱的金发簪,但因为生活窘迫,不得不变卖了换来全家的口粮。年幼时的我自然不懂这破铜板如何是钱,能买东西?也不知道金簪怎么舍得换大米?但我知道外婆放在樟木箱里用手帕包卷着的黄绿票子能给我买酸甜的山楂片,过年时会成为我的压岁钱。有时我也会盯着外婆小心打开放入或取出钱,然后再将它们小心包好,仔细放好,这才合上箱门。当铜钥匙从锁眼中拔出,又躺回它原来的地方时,我就知道那个樟木箱又恢复成我的神秘探索宝库了。
后来,外婆会带我去有着高高柜台的银行存钱,我的小猪扑满肚子里倒出的大大小小的薄分币也能换成一角、五角纸币。那是我的小宝库,如同外婆的樟木箱子。大人们有时会给我些零钱,我的宝库塞满了纸币与分币反倒听不清那清脆的钱币在粗陶扑满中摇晃的声音,但我陶醉于幸福的满足感中。
小学五年级,一位家人在银行工作的同学打开一块手帕,里面是几枚簇新的一角、五角硬币。这刚发行的硬币有着漂亮的细致雕花,小巧玲珑,引得我们好生羡慕,正要伸手,她却将手帕一收,生怕我们触摸后硬币会失去亮泽。
上了初中,硬币已不是稀罕之物。我常与同桌去学校外围小卖部买点心,一元硬币能买四个小生煎包。那时,女生们喜欢往花布小零钱包里放很多硬币,家中的储钱罐早已不知所踪。而外婆的樟木箱子在我眼中也不再神秘,倒有些不入时的土旧。但外婆依然会把她认为宝贝的东西锁进去,依然会取出钱来填塞我的压岁包。
等到我去异地上大学后,每回离家前,外婆便会用那把已弯旧黯沉的铜钥匙打开吱哑的箱门,塞给我几张崭新的红票子。我让外婆自己留着,她却说一人在外别太省,看你瘦得,要多吃点啊。我告诉她爸妈每月会往我的银行卡上汇钱,学校有自动取款机,取钱很方便,不缺钱,可外婆仍揣进我口袋里。她不舍得自己花,花在小辈身上比自己用更开心。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流失,恍然间我发现樟木箱已不再被开启,钥匙静静地躺在某个角落。我开始怀念那个黑锁孔,那只灰色铁皮箱,企盼它再次被翻开,再次打开那方蓝格子手帕。
几年后,母亲拿来红绳长命锁和转运珠,叮嘱我小心保管,因为那是外婆弥留之际托母亲给我小宝提前准备的诞生礼,就一直存放在樟木箱内。
小宝长大了,他有一只红色绒布百宝箱,里面放着那串转运珠和红绳锁片。他还有一只塑料扑满,上面有他可爱的照片。他如同我小时候一样,饶有兴致地放进去一个又一个硬币,再倒出来细细数。他知道妈妈买东西会用手机,可他更喜欢自己拥有的小宝库,那是家人给他的零币,在他看来却是了不得的财富。他时常好奇地歪着脑袋瞅着那道狭长的缝往里瞧,如同小时候的我踮着脚尖儿瞄着那只樟木箱上的铜锁眼……
时代在前进,货币的结算方式在发展。从樟木箱到零钱罐,小小钱币上的变迁,既有亲情的传承,也有亲人的怀念,随着时光的轮回,国之爱、家之爱的情结也一直在延伸……
(太仓农商银行 陆文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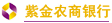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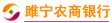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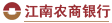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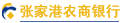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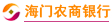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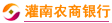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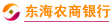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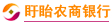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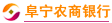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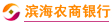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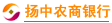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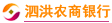












 2025年07月18日
2025年07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