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看详情
散文:《耕田》
更新时间:2018-08-30
“驾、驾、驾”“哟、哟、哟”“嗬、嗬、嗬”……爷爷歪着头,扶着犁,吆喝着牛,偶尔,抽上一鞭子。老水牛,低着头,拱着肩,鼓着大肚子,四脚平稳,一步套一步,向前。黑亮油光的土块,一片片在犁下翻吐开来,像瓦片,整齐地扣在田里。稻田是黄的,泥是黑的,黑黄之间,牛和爷爷,成了细线上的两点,像个冒号……
爷爷是个种田的好把式。他养着队里的大水牛。到耕种季节,他是最繁忙的,队里的大小田块,都要他一犁一犁耕过去。他耕得好,整天忙个不息,你家请,他家请,前后有半个月,爷爷都不用在家吃一顿饭。
牛是人养的。爷爷养牛,一天之中,除了吃饭睡觉,他都和牛在一起。有时,睡,他也睡在牛棚里。牛饥牛渴牛病痛,他知道;牛喜牛乐牛发脾气,他也知道。他喂它,精心侍候它。牛劳累时,他给它加餐,他把黄豆托在手心,让牛舔着吃……
他喜欢牛,牛也顺从他。只要他耕田,牛都能按照他的意思,走得笔直,耕出来的田,就有模有样,好看。当然,牛也知道,它一歪,鞭子就会落下来。牛也是不肯给别人牵的,到别人那里,牛就没那么听话了。有时,有人把牛牵走,耕完地再送回来。可那地,歪歪扭扭,土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不用标明,人们走在田边,就知道这不是“有圣叔”(有圣是爷爷的名)耕的田。
犁,是铁铸的,有几十斤重。扶犁耕田,既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后来两年,爷爷年岁上升了,力气大不如从前。爷爷犁完一陇,到田头,掉转再犁,就没有以前那样灵活了。有时,要停下,喘一会儿,停一会儿。汗水湿漉漉的,沿着他的额发,往下滴。他甩掉草帽,擦擦汗,再犁。犁到田中央,他洗得发白的灰色褂子,背后湿了一个大圆圈。不到晌午,他的衣衫就湿透了。那衣衫紧贴在他的身上,显出他干瘦的肋骨。“越来越会流汗了!”他一边擦汗,一边不满地说——他对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满。
奶奶叫他回去歇歇,他总是不肯:这块地耕完了再说。奶奶叫他别再养牛了。“过了这一熟,再说!”他总想自己还行,他不会想到,病魔悄无声地,罩着他了。
为了抢收抢种,耕田劳累,他经常顾不及吃饭,有时,来叫他吃饭的人,来回田头许多次,他才肯上岸,到人家也只是匆匆吃两口。有时,干脆,等活做完再吃。就这样饱一顿,饥一顿,有一顿,没一顿。爷爷终于在花甲之年,再也不能扶犁了。
不能扶犁的爷爷,穿着肥大的衫裤,常站在田边出神,地里没有人,庄稼也没长。那些别人犁过的地,虽不规整,但也能种麦。爷爷就那样站在田头,野风吹乱他的白发,远远望去,像地头竖起的一根杆子。又像一个感叹号。
丫丫和奶奶轮番叫他,爷爷才慢慢吞吞,手背在背后,偻着腰,回来。
爷爷于第二年,就走了,憩息了。
爷爷八大个子,四方脸,双目炯炯,有络腮胡子。他那粗壮的大手,把丫丫举上过牛背,托进牛窠。高兴时,他还把丫丫掼到半空中,然后放下,用胡茬扎她,惹得她咯咯笑。
丫丫稍大,他教她喂牛、放牛。如果他不是那样早就走了,如果丫丫是个男孩,那他一定会教她耕田的。
不会耕田的丫丫长大了,每当肩上感到沉重时,就会想到爷爷,想到站在田边看到的那一幕,那田中间,人与牛构成的冒号。
(如东农商银行 苏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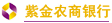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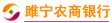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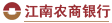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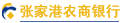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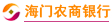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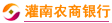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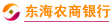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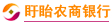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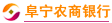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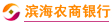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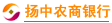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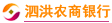












 2025年07月18日
2025年07月18日





